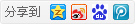大鹏 电影里有我的答案
时间:2020-09-08 07:35:28 来源:天津日报
[导读]大鹏 著名导演、演员,1982年生于吉林省集安市,曾做过网站主持人,编剧、导演电影《煎饼侠》《缝纫机乐队》《吉祥如意》,主演电影《铤而...
大鹏 著名导演、演员,1982年生于吉林省集安市,曾做过网站主持人,编剧、导演电影《煎饼侠》《缝纫机乐队》《吉祥如意》,主演电影《铤而走险》《受益人》《第八个嫌疑人》《大赢家》等。
拍电影记录
姥姥家过年聚会
近日,从上海电影节到北京电影节,大鹏导演的新作《吉祥如意》频频亮相引起关注。这部电影讲述一位喜剧片导演突发奇想,回到东北农村老家,希望将一家人如何过年拍成电影,结果遭遇一系列意外,体现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亲情。
这部半纪录片式的电影是大鹏的亲身经历,片中人物也都是他姥姥家的亲戚。大鹏出生在吉林省集安市,父亲是机械厂工人,母亲是市评剧团演员,在大鹏很小的时候,母亲得了肾炎,常去大城市治疗,大鹏从小在姥姥身边长大。他不仅对姥姥有着深厚感情,也深知自己家人对姥姥的依赖,尤其是因中年得病而生活无法自理的三舅王吉祥。他想要拍一部有演员却没有情节的故事片,记录姥姥家的过年聚会,找来演员刘陆以家庭成员身份加入到聚会中,然而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这些事也被拍进了电影。
《吉祥如意》首映过后,观众反响热烈,有人惊艳于影片实验性的、独特的表达形式和叙事结构,也有人感动于故事中真挚朴实的情感,并引发了大家对于亲情的思考。大鹏说:“在电影当中大家会看到我本人,除了导演的身份,我也是被记录者。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家人永远是我们的依靠,还是那句话,常回家看看。”
大鹏小时候的梦想并不是做电影导演,从吉林建筑大学毕业后,他到北京做了一名网站编辑,在完成了一次次职业转换后,慢慢在电影领域站稳脚跟。他说:“我只有一个招数,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只要是正确的方向,不怕慢慢走,总会到达。”尽管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人加速前进,但是他依然选择有点儿笨拙的方式,简单而缓慢地实现着内心的每一个梦想。
谈到喜剧,大鹏认为所有的喜剧都需要精确的计算,“相比于感性,它更倾向于理性,相比于文科,它更倾向于理科,是有一套公式的,但是掌握这套公式的人,可能在华语语境中凤毛麟角。我个人觉得在喜剧的探索上,我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前面有很多前辈那么优秀,他们的存在,督促我还会继续创作。”
《吉祥》的观影疑问
会在《如意》中找到答案
记者:您之前拍过一部短片叫《吉祥》,当大家看到《吉祥如意》这个片名的时候,会问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
大鹏:它是一个短片的加长版。2016年我们创建剧组,跟剧组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签订了保密协议,我们协定好,不会透露我们在做什么样的电影,怎么去拍,以及拍摄什么故事。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确定了《吉祥如意》的结构是由《吉祥》加上《如意》的部分,《吉祥》就是那部已有的短片,变成了整个长片里面的一部分。在《吉祥》的观影过程中,观众会提出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会在《如意》的部分找到解答。这样一个完整的长片电影,很难用到底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去界定。里面大部分人都是生活当中我的家人,他们在电影中的角色就是他们自己,但是我们有一个演员承担表演工作,就是刘陆,所以这是一次比较有实验性的探索,也会提供给观众一种很新颖的互动交流的观影体验。
记者:最早想要拍这部电影是如何考虑的?
大鹏:2016年我们在为《缝纫机乐队》做准备,《缝纫机乐队》里面最大的一个场景是吉他雕塑,要准备半年时间,我们回到我的老家吉安,我去了我姥姥家。我小时候是跟姥姥长大的,我的母亲常年生病,到全国各地求医问药,我的童年记忆都是跟我姥姥在一起。我来到姥姥家,看到一面墙,墙上有很多照片,是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在不同时间点的合影。那些照片记录着这一家人一起走过的很多共同的经历。当我再次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我的感受很奇妙,我想如果说静态的影像能有这么强大的力量的话,是不是我可以用我的摄制团队来记录一下姥姥家是怎么过年的?
记者:这部电影的拍摄、制作过程长达四年,您也说过这部电影对您非常特殊,那么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特殊的记忆?
大鹏:我觉得作为导演,未来还有机会拍其他影片,但是这一次拍《吉祥如意》,在我的工作经历当中是非常特别的,几乎是不可复制的,它是一部电影,同时也是所有参与这部电影制作的工作人员的一段经历。因为我没有剧本,发生什么就捕捉什么,我跟所有的剧组工作人员说,我们要拍一场“天意”,我不去干涉大家说的话,也不去干涉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再把我们所有的拍摄过程再拍摄下来。我们成立了两个剧组,一个是《吉祥》,一个是《如意》,一个是我来拍这部电影,一个是拍我怎么拍这部电影。说起来比较拗口。当我们整个剧组回到农村老家,当我们正式开始拍摄,这个家庭遭遇了一个又一个意外,这个意外的量级,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最重要的事情,当我们面对这些意外,我想起出发的时候是要拍“天意”,发生什么就拍什么,于是我们就进行下去,于是呈现出来了现在的《吉祥如意》。
看完《吉祥如意》
希望大家常回家看看
记者:您自己最想通过《吉祥如意》表达什么?
大鹏:这部电影的素材量是80个小时,我也参与了剪辑,每个素材、每个镜头、每句话已经反复在剪辑台上挪动了位置,所以对我来讲非常熟悉。我猜想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可能集中讨论的会是年夜饭的时候,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场面,那个场面长达8分钟,大家说着说着突然就吵了起来,大家的争吵过渡得是那么没有痕迹,甚至当我们注意到这是一场争吵的时候,都忘了最开始的导火索是从什么时候点燃的。它呈现在电影里面是8分钟,事实上持续的时间更久。可是,第二天发生了什么呢?就是一家人相约在阳光下,一起照了一张全家福,然后大家露出了笑容。所以这就是家人,这就是家,在一个又一个事件当中,在漫长的时间里,互相编织的那种柔韧的关系,所以我很感激我的家人。
记者:把自己家里的私事搬到大银幕上其实需要勇气,您的家人会不会给您施加什么压力,能不能理解您?
大鹏:在拍摄过程当中,以及后面的制作过程当中,其实所有的家人没有表示出要干预以及反对,这正是源自我是他们的家人,也是一种信任。每次看到素材,包括呈现在大银幕上,我都很感激、感动,因为我的家人们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是出租车司机,以及在北京“北漂”承受很多压力的普通人,他们从来没有对我的电影创作提出过异议,他们大多都看了最后的成片,没有针对里面的哪些内容来找我探讨,要求我修改。包括我自己,也是成片里面的故事之一,可能大家在成片里也看到了与大家期待或想象中完全不同的我的样子。我们总是在思考,迈出这一步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但是如果大家看完这部电影后想到了自己的家庭,想到自己应该在有时间、精力、条件的情况下常回家看看,可能就是我们做这部电影的价值。
记者:这四年当中有没有想过放弃?
大鹏:我想说电影里面有答案。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意外,但即使没有这些意外,这部电影也会诞生,只不过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对于生活当中我本人来讲,我宁愿拍的不是这样的电影。
不想用已有概念
去定义这部电影
记者:《吉祥如意》纪录片和剧情片混合拍摄,对您来说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您觉得有哪些挑战,哪些突破?
大鹏:当我接触这个内容的时候,完全是遵循心里面的节奏,我觉得它应该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并没有把它主观地分为这是纪录片的部分,这是剧情片的部分,我没有主观下这个定义,《吉祥如意》到底是什么样的类型,我觉得可能观众看完后会有自己的答案,重要的是我们没有拘泥于已有的概念去定义这部电影。
记者:您不是学院派的导演,那么在拍摄技法上有什么不一样?
大鹏:《吉祥如意》在上海电影节观影结束现场交流的时候,有一位观众,他是学电影的,问了我一个问题,用了很多我其实有些陌生的名词,来定义我自己拍过的内容。我都没想过原来那个概念是那样去描述的。他问我具体的技巧和思路,我说我其实不是学电影的,我没有你那么幸运,我热爱电影,我从小就看电影,我希望自己有机会从事这个工作,但我没有那个机会去系统地学习电影,我所有拍摄的方式都是和我的合作伙伴共同摸索出来的,都是在我作为导演的实践当中去学到的。
记者:《吉祥如意》可能更接近于文艺片,您对票房有什么期待?
大鹏:我看到一些新闻报道描述这部电影,会用到“私人影像”这个词,其实这是不可否认的,它是我的个人经历和我的家庭在一个比较集中的时间段内发生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种情感是普遍的,我们都是独生子女一代,我们的父母有兄弟姐妹,我们每次回家过年会遇到一个庞大的家族,然后有各种讨论。所以我对这部电影的未来和大家的接受程度,以及观众的反馈,是有非常正向的期待的。在我自己的定义当中,不仅没有纪录片和剧情片的界限,也没有文艺片和商业片的界限,它就是一部电影,然后大家走到电影院去感受这个情感。我对它的票房甚至都充满期待,因为我觉得它并不一定像我们印象当中的那样,这样一部电影票房就会很冷,我觉得变化也许会从这部电影开始。
记者:现在大家都呼吁观众回到电影院,您觉得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和在家看电影有什么不一样?
大鹏:我们当然可以在手机上看电影,可以把电影投到电视里面跟家人分享,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一个陌生的空间和一群陌生的人,一起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内容。当我们想笑的时候,坐在旁边的那个人会不会因为我笑了以后他也发笑?当我们想流泪的时候,我会不会不好意思?然后我看到他哭了,我也释放了。我觉得这个是电影需要去电影院看的重要原因。在观影过程当中,那样一群人在这样一个空间,看到他们完全没有预知的故事,他们被这个情感打动,产生共振,我觉得这是最奇妙的。
制片人陈祉希谈大鹏
他有更多的能量
想去尝试更多创意
我跟大鹏导演有过多次合作,从《煎饼侠》到《缝纫机乐队》,但是当导演跟我说要做《吉祥如意》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有点儿蒙。不过我特别了解导演,因为一直陪伴他做电影,之前做的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商业喜剧,而他一直是一位希望探索更多可能性的导演,他不想局限于喜剧演员或者喜剧表演这样的标签,他有更多的能量,想去尝试更多的创意。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支持导演去创作这样一个作品。
《吉祥如意》想拍一个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女孩,过年回家,姥姥会做怎样的年夜饭,会给大家带来什么。大鹏导演去他的老家采景,跟姥姥告别离开的时候,村里很多人来跟他合影,他没来得及跟姥姥告别,心里想的是,我很快就要回来拍电影了,很快就会再见到姥姥了。但是……当导演准备拍摄的时候,姥姥摔了一跤,进了医院,之后没再醒过来……所以……没有办法拍姥姥,导演没有再见到姥姥。
但是,电影还是要拍下去,这也是对姥姥的纪念。我们这个过程持续了四年,是因为每一次打开素材,对大鹏导演来说,都是又一次打开了伤痛,又一次让他接受那样一个场面和那样一种情境。我见过他在剪辑台前剪着剪着说“我很崩溃”,因为这是一个特别艰难的创作过程。大鹏导演是一个把情感埋藏得很深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很有责任感,很有担当的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放弃,但他还是咬牙,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有一位观众看了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抹眼泪,他说他想起了两年前去世的爷爷。听到这句话,我觉得观众明白了我们为什么去做这样的电影。
我问过大鹏导演,你把自己家里的故事拿出来给观众看,这其实要背负非常大的压力,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勇气?他说,其实就是想说常回家看看,就像电影里的主人公三舅经常唱“常回家看看”。现在有太多人离开家乡,很多年没回去,就像大鹏导演本人,一直在追求梦想,只能偶尔回去,当他付出行动,想回家去拍一个大家一起吃年夜饭的电影,姥姥已经不在了……我想观众会在电影里找到答案,希望大家都能常回去看看自己的家人,我相信大家看过这部电影以后,会有更深的感触。
我们通常觉得,非常个人的表达难以让观众产生共鸣,但恰恰《吉祥如意》这部电影是非常个人的表达,但我相信观众能够感受到。这就是它最特别的地方。
拍电影记录
姥姥家过年聚会
近日,从上海电影节到北京电影节,大鹏导演的新作《吉祥如意》频频亮相引起关注。这部电影讲述一位喜剧片导演突发奇想,回到东北农村老家,希望将一家人如何过年拍成电影,结果遭遇一系列意外,体现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亲情。
这部半纪录片式的电影是大鹏的亲身经历,片中人物也都是他姥姥家的亲戚。大鹏出生在吉林省集安市,父亲是机械厂工人,母亲是市评剧团演员,在大鹏很小的时候,母亲得了肾炎,常去大城市治疗,大鹏从小在姥姥身边长大。他不仅对姥姥有着深厚感情,也深知自己家人对姥姥的依赖,尤其是因中年得病而生活无法自理的三舅王吉祥。他想要拍一部有演员却没有情节的故事片,记录姥姥家的过年聚会,找来演员刘陆以家庭成员身份加入到聚会中,然而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这些事也被拍进了电影。
《吉祥如意》首映过后,观众反响热烈,有人惊艳于影片实验性的、独特的表达形式和叙事结构,也有人感动于故事中真挚朴实的情感,并引发了大家对于亲情的思考。大鹏说:“在电影当中大家会看到我本人,除了导演的身份,我也是被记录者。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家人永远是我们的依靠,还是那句话,常回家看看。”
大鹏小时候的梦想并不是做电影导演,从吉林建筑大学毕业后,他到北京做了一名网站编辑,在完成了一次次职业转换后,慢慢在电影领域站稳脚跟。他说:“我只有一个招数,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只要是正确的方向,不怕慢慢走,总会到达。”尽管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人加速前进,但是他依然选择有点儿笨拙的方式,简单而缓慢地实现着内心的每一个梦想。
谈到喜剧,大鹏认为所有的喜剧都需要精确的计算,“相比于感性,它更倾向于理性,相比于文科,它更倾向于理科,是有一套公式的,但是掌握这套公式的人,可能在华语语境中凤毛麟角。我个人觉得在喜剧的探索上,我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前面有很多前辈那么优秀,他们的存在,督促我还会继续创作。”
《吉祥》的观影疑问
会在《如意》中找到答案
记者:您之前拍过一部短片叫《吉祥》,当大家看到《吉祥如意》这个片名的时候,会问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
大鹏:它是一个短片的加长版。2016年我们创建剧组,跟剧组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签订了保密协议,我们协定好,不会透露我们在做什么样的电影,怎么去拍,以及拍摄什么故事。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确定了《吉祥如意》的结构是由《吉祥》加上《如意》的部分,《吉祥》就是那部已有的短片,变成了整个长片里面的一部分。在《吉祥》的观影过程中,观众会提出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会在《如意》的部分找到解答。这样一个完整的长片电影,很难用到底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去界定。里面大部分人都是生活当中我的家人,他们在电影中的角色就是他们自己,但是我们有一个演员承担表演工作,就是刘陆,所以这是一次比较有实验性的探索,也会提供给观众一种很新颖的互动交流的观影体验。
记者:最早想要拍这部电影是如何考虑的?
大鹏:2016年我们在为《缝纫机乐队》做准备,《缝纫机乐队》里面最大的一个场景是吉他雕塑,要准备半年时间,我们回到我的老家吉安,我去了我姥姥家。我小时候是跟姥姥长大的,我的母亲常年生病,到全国各地求医问药,我的童年记忆都是跟我姥姥在一起。我来到姥姥家,看到一面墙,墙上有很多照片,是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在不同时间点的合影。那些照片记录着这一家人一起走过的很多共同的经历。当我再次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我的感受很奇妙,我想如果说静态的影像能有这么强大的力量的话,是不是我可以用我的摄制团队来记录一下姥姥家是怎么过年的?
记者:这部电影的拍摄、制作过程长达四年,您也说过这部电影对您非常特殊,那么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特殊的记忆?
大鹏:我觉得作为导演,未来还有机会拍其他影片,但是这一次拍《吉祥如意》,在我的工作经历当中是非常特别的,几乎是不可复制的,它是一部电影,同时也是所有参与这部电影制作的工作人员的一段经历。因为我没有剧本,发生什么就捕捉什么,我跟所有的剧组工作人员说,我们要拍一场“天意”,我不去干涉大家说的话,也不去干涉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再把我们所有的拍摄过程再拍摄下来。我们成立了两个剧组,一个是《吉祥》,一个是《如意》,一个是我来拍这部电影,一个是拍我怎么拍这部电影。说起来比较拗口。当我们整个剧组回到农村老家,当我们正式开始拍摄,这个家庭遭遇了一个又一个意外,这个意外的量级,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最重要的事情,当我们面对这些意外,我想起出发的时候是要拍“天意”,发生什么就拍什么,于是我们就进行下去,于是呈现出来了现在的《吉祥如意》。
看完《吉祥如意》
希望大家常回家看看
记者:您自己最想通过《吉祥如意》表达什么?
大鹏:这部电影的素材量是80个小时,我也参与了剪辑,每个素材、每个镜头、每句话已经反复在剪辑台上挪动了位置,所以对我来讲非常熟悉。我猜想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可能集中讨论的会是年夜饭的时候,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场面,那个场面长达8分钟,大家说着说着突然就吵了起来,大家的争吵过渡得是那么没有痕迹,甚至当我们注意到这是一场争吵的时候,都忘了最开始的导火索是从什么时候点燃的。它呈现在电影里面是8分钟,事实上持续的时间更久。可是,第二天发生了什么呢?就是一家人相约在阳光下,一起照了一张全家福,然后大家露出了笑容。所以这就是家人,这就是家,在一个又一个事件当中,在漫长的时间里,互相编织的那种柔韧的关系,所以我很感激我的家人。
记者:把自己家里的私事搬到大银幕上其实需要勇气,您的家人会不会给您施加什么压力,能不能理解您?
大鹏:在拍摄过程当中,以及后面的制作过程当中,其实所有的家人没有表示出要干预以及反对,这正是源自我是他们的家人,也是一种信任。每次看到素材,包括呈现在大银幕上,我都很感激、感动,因为我的家人们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是出租车司机,以及在北京“北漂”承受很多压力的普通人,他们从来没有对我的电影创作提出过异议,他们大多都看了最后的成片,没有针对里面的哪些内容来找我探讨,要求我修改。包括我自己,也是成片里面的故事之一,可能大家在成片里也看到了与大家期待或想象中完全不同的我的样子。我们总是在思考,迈出这一步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但是如果大家看完这部电影后想到了自己的家庭,想到自己应该在有时间、精力、条件的情况下常回家看看,可能就是我们做这部电影的价值。
记者:这四年当中有没有想过放弃?
大鹏:我想说电影里面有答案。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意外,但即使没有这些意外,这部电影也会诞生,只不过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对于生活当中我本人来讲,我宁愿拍的不是这样的电影。
不想用已有概念
去定义这部电影
记者:《吉祥如意》纪录片和剧情片混合拍摄,对您来说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您觉得有哪些挑战,哪些突破?
大鹏:当我接触这个内容的时候,完全是遵循心里面的节奏,我觉得它应该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并没有把它主观地分为这是纪录片的部分,这是剧情片的部分,我没有主观下这个定义,《吉祥如意》到底是什么样的类型,我觉得可能观众看完后会有自己的答案,重要的是我们没有拘泥于已有的概念去定义这部电影。
记者:您不是学院派的导演,那么在拍摄技法上有什么不一样?
大鹏:《吉祥如意》在上海电影节观影结束现场交流的时候,有一位观众,他是学电影的,问了我一个问题,用了很多我其实有些陌生的名词,来定义我自己拍过的内容。我都没想过原来那个概念是那样去描述的。他问我具体的技巧和思路,我说我其实不是学电影的,我没有你那么幸运,我热爱电影,我从小就看电影,我希望自己有机会从事这个工作,但我没有那个机会去系统地学习电影,我所有拍摄的方式都是和我的合作伙伴共同摸索出来的,都是在我作为导演的实践当中去学到的。
记者:《吉祥如意》可能更接近于文艺片,您对票房有什么期待?
大鹏:我看到一些新闻报道描述这部电影,会用到“私人影像”这个词,其实这是不可否认的,它是我的个人经历和我的家庭在一个比较集中的时间段内发生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种情感是普遍的,我们都是独生子女一代,我们的父母有兄弟姐妹,我们每次回家过年会遇到一个庞大的家族,然后有各种讨论。所以我对这部电影的未来和大家的接受程度,以及观众的反馈,是有非常正向的期待的。在我自己的定义当中,不仅没有纪录片和剧情片的界限,也没有文艺片和商业片的界限,它就是一部电影,然后大家走到电影院去感受这个情感。我对它的票房甚至都充满期待,因为我觉得它并不一定像我们印象当中的那样,这样一部电影票房就会很冷,我觉得变化也许会从这部电影开始。
记者:现在大家都呼吁观众回到电影院,您觉得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和在家看电影有什么不一样?
大鹏:我们当然可以在手机上看电影,可以把电影投到电视里面跟家人分享,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一个陌生的空间和一群陌生的人,一起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内容。当我们想笑的时候,坐在旁边的那个人会不会因为我笑了以后他也发笑?当我们想流泪的时候,我会不会不好意思?然后我看到他哭了,我也释放了。我觉得这个是电影需要去电影院看的重要原因。在观影过程当中,那样一群人在这样一个空间,看到他们完全没有预知的故事,他们被这个情感打动,产生共振,我觉得这是最奇妙的。
制片人陈祉希谈大鹏
他有更多的能量
想去尝试更多创意
我跟大鹏导演有过多次合作,从《煎饼侠》到《缝纫机乐队》,但是当导演跟我说要做《吉祥如意》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有点儿蒙。不过我特别了解导演,因为一直陪伴他做电影,之前做的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商业喜剧,而他一直是一位希望探索更多可能性的导演,他不想局限于喜剧演员或者喜剧表演这样的标签,他有更多的能量,想去尝试更多的创意。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支持导演去创作这样一个作品。
《吉祥如意》想拍一个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女孩,过年回家,姥姥会做怎样的年夜饭,会给大家带来什么。大鹏导演去他的老家采景,跟姥姥告别离开的时候,村里很多人来跟他合影,他没来得及跟姥姥告别,心里想的是,我很快就要回来拍电影了,很快就会再见到姥姥了。但是……当导演准备拍摄的时候,姥姥摔了一跤,进了医院,之后没再醒过来……所以……没有办法拍姥姥,导演没有再见到姥姥。
但是,电影还是要拍下去,这也是对姥姥的纪念。我们这个过程持续了四年,是因为每一次打开素材,对大鹏导演来说,都是又一次打开了伤痛,又一次让他接受那样一个场面和那样一种情境。我见过他在剪辑台前剪着剪着说“我很崩溃”,因为这是一个特别艰难的创作过程。大鹏导演是一个把情感埋藏得很深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很有责任感,很有担当的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放弃,但他还是咬牙,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有一位观众看了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抹眼泪,他说他想起了两年前去世的爷爷。听到这句话,我觉得观众明白了我们为什么去做这样的电影。
我问过大鹏导演,你把自己家里的故事拿出来给观众看,这其实要背负非常大的压力,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勇气?他说,其实就是想说常回家看看,就像电影里的主人公三舅经常唱“常回家看看”。现在有太多人离开家乡,很多年没回去,就像大鹏导演本人,一直在追求梦想,只能偶尔回去,当他付出行动,想回家去拍一个大家一起吃年夜饭的电影,姥姥已经不在了……我想观众会在电影里找到答案,希望大家都能常回去看看自己的家人,我相信大家看过这部电影以后,会有更深的感触。
我们通常觉得,非常个人的表达难以让观众产生共鸣,但恰恰《吉祥如意》这部电影是非常个人的表达,但我相信观众能够感受到。这就是它最特别的地方。
编辑:zmh
关键字:
声明:网上天津登载此文出于传送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网友参考,如有侵权,请与本站客服联系。信息纠错: QQ:9528213;1482795735 E-MAIL:148279573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