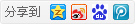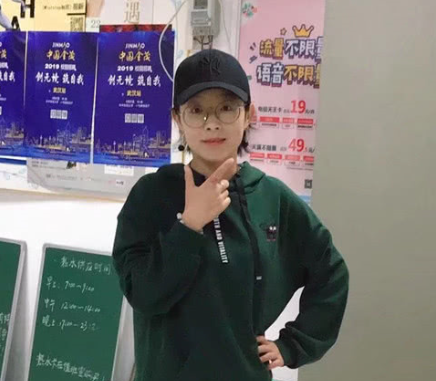画家叶永青涉嫌剽窃事件引关注 艺术生涯从头开始?
时间:2019-04-25 07:43:44 来源:北京青年报
[导读]叶永青涉嫌剽窃希尔万作品一事广受关注偷来的艺术生涯只能从零开始?左:劳伦·娜瑟夫的设计右:萨曼萨·比特森的参赛作品凯特·伍吉作品被迪斯尼窃用周二·巴森的设计遭Zara“借鉴”◎李树波一个埋了30年的定时炸弹近期被引爆,冲击波从比利时当地报纸和电视台炸开,延伸到法国媒体、Twitter、《南华早报》以及其他媒体。
叶永青涉嫌剽窃希尔万作品一事广受关注
偷来的艺术生涯只能从零开始?

左:劳伦·娜瑟夫的设计 右:萨曼萨·比特森的参赛作品

凯特·伍吉作品被迪斯尼窃用

周二·巴森的设计遭Zara“借鉴”
◎李树波
一个埋了30年的定时炸弹近期被引爆,冲击波从比利时当地报纸和电视台炸开,延伸到法国媒体、Twitter、《南华早报》以及其他媒体。一个月之内,全世界人民都听到了比利时画家克里斯托安·希尔万的指控:中国画家叶永青30年来一直剽窃其作品,瞒天过海,获利甚丰。
毕加索说过,“好艺术家抄,大艺术家偷。”
所谓偷,是妙手空空,从人家画中抓取最高妙的部分,变成自己的东西。拿毕加索做个例子吧,毕加索在喀麦隆面具的极端抽象中加入高更的大溪地女子风情,以塞尚的大浴女题材为载体,画出了《阿维尼翁的少女》。他从好友勃拉克的画里相继析出立体主义和拼贴画的创作方法,受害者心里苦又没法找茬,只能对毕加索严防死守。
抄呢,则是老老实实临摹对方,做自己的作业。
丰子恺通过学习日本画家竹久梦二,开创出用简笔画表达人文感慨和社会风貌的新路子,一举成为上海最受瞩目的漫画家。但丰子恺的感受和表达都是他自己的,竹久梦二只是和他心灵气质契合的前辈,指引出一个朦胧的方向,路终究还是要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
叶永青和希尔万的作品从整体结构,到层次母题、符号使用、笔墨气质,相似度如何,相信广大读者自有判断。
剽窃这件事,中西都有。但是西方社会对此事的态度还是很鲜明的,可能有法律未覆盖的不管地带,但是对于剽窃的行为本身不存在认知上的灰色地带。一旦被抓住,剽窃者如果不想改名换姓还要混下去,除了立即检讨道歉外没有别的出路。
剽窃完全能毁掉一个艺术家的名望
一般来说,剽窃造假的事被曝光后无非三个后果:身败名裂、法律诉讼和金钱赔偿。
在欧洲,剽窃完全能毁掉一个艺术家的名望,想继续从事这个行业,就只能从零开始。2012年,英国诺福克郡冉冉升起一颗艺术新星:拉仕迪·巴勒特。这个年轻人灵感如泉涌,不断创作出清新别致的插画作品,在网上广为流传,还被邀请在美国弗吉尼亚当代艺术博物馆开了个展。就在他的第三个个展期间,有人指出,他的一幅画和巴西艺术家马修·洛佩兹·卡斯特罗的插画如出一辙。画廊的策展人索马斯得知此事后,震惊之余赶紧去查巴勒特的其他作品。这一查不要紧,巴勒特展出过、卖掉的作品基本来自六位艺术家,或者原封不动,或做了些微小改动。
索马斯愤怒地表示:“他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尊重、认可和投资,本来应该给那些正正经经做艺术的人。”
另一位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为巴勒特办过展览的画廊主管也表示:“做一个全职艺术家意味着无法估量的心智能量投入和近乎疯狂的时间投入。这些被抄袭的艺术家下了苦功,才创作出这样有吸引力的艺术语言。这件事一定要广而告之,让大家都能发表意见。”
“偷来的艺术生涯”这个标签就此被贴在了拉仕迪·巴勒特身上。尽管他后来通过公开道歉,迅速给抄袭丑闻画上了句号,但他基本只能回去干老本行DJ,虽然还画一些画,却已不再自称艺术家了。
希尔万和叶永青二者之间的问题则只能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过去二十年里,希尔万先后三次通过中间机构向展出叶永青的画廊投诉,而叶永青及其画廊未能及时有效地予以回应。现在这类情况可能面临怎样的局面呢?
根据国际知识产权法的规定,首先要确认侵权行为的发生。受害人要就以下三点进行举证:第一:受害者拥有有效版权。希尔万创作这些作品的行为应没有疑问。
第二,受害人要证明侵权者有途径接触到这些被侵权的作品。在希尔万基金会所收集的材料中,叶永青画室里赫然有两幅希尔万的作品挂在墙上。叶永青也承认过希尔万对他影响至深。
第三,此侵权行为不属于可以特殊对待的例外情况。国际知识产权法会在产权拥有者和被保护产品的使用者之间适当平衡,并允许不同国家对知识产权的限制和例外情况做出适合本国情况的规定。一般来说,教育机构、图书馆和残障人士(尤其是视觉障碍)能够在未经授权就使用知识产权时得到一些豁免和优惠。叶永青对希尔万的侵权显然不属于这一类例外情况。
那么一旦确认,侵权人将受到怎样的惩罚呢?根据国际知识产权法,可以有以下预期:一、损害赔偿金和利润损失的确切数额的民事赔偿金(每件侵权物赔偿金额从200美元到150000美元不等);二、禁止侵权人继续其非法活动的禁令;三、扣押或没收侵权作品;四、监禁;五、被告强制支付法院和律师费。看来,不管是和解还是判决,这个案子的标的都小不了。
大卫和巨人歌利亚之战——独立小设计师沦为大品牌的免费创意库
在欧洲,艺术家被剽窃的事情常见吗? 搞纯艺术的人里很少,做工艺美术设计或者插画等商业美术领域里倒很常见。搞纯艺术的人本来就不屑于走大多数人走的路,要标新立异,性格比较独,家里又不缺钱,于是不怕穷不怕苦投入这行,根本不屑于抄袭。从事商业艺术的则比较能感受到挣钱的压力,头脑也比较灵活,又善于说服别人说服自己,于是有的人就在“借鉴”别人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了。
英国法尔莫斯大学纺织设计系毕业生萨曼萨·比特森赢得了纺织图案大奖,除了奖金之外,她还获邀在香港和巴黎行业展会上出售自己的设计,锦绣前程就在眼前。但几天后,住在芝加哥的艺术家和插画师劳伦·娜瑟夫的博客里有人留言,说你的插画可能被人偷了。有个英国学生把你的插画用在她的设计里拿了大奖。劳伦·娜瑟夫展开了调查,她发现萨曼萨·比特森的设计就是把自己笔下24幅作品里的人物和元素一网打尽,重新排列组合,甚至还临时编了一个灵感速写本,表示所有创作都来自生活积累和日常灵感。
劳伦·娜瑟夫立即联系了所有相关人士:比特森的学校、颁奖机构以及转帖、赞美比特森获奖作品的博主们。比特森的名字从获奖名单里被删除,有关博客也被删掉。也许因为对方还是个学生,娜瑟夫并没有要求进一步赔偿。
要是你以为只有初出茅庐的学生才干这种事,就大错特错了。视觉剽窃的重灾区是绘画、设计、手工网络社群平台,比如Art Station, Deviant Art, Esty, 本来是同好分享最新创作、也出售作品的文创社区,近年来却频频遭遇大公司和知名品牌的黑手。
住在英格兰南部的凯特·伍吉是Deviant Art上的红人。2010年,她还在美院读书,以《爱丽丝漫游奇境》为灵感,画了一幅爱丽丝在镜中把玫瑰涂红的插画,发表在博客上,收获了无数赞美,至少有九个人把这幅画原样纹到了自己的皮肤上。迪斯尼也看上了它,把它用在周边产品:化妆包和T恤上,但没有通知凯特,也没有给她一分钱。凯特联系迪斯尼的邮件也如石沉大海。毕竟,迪斯尼认为它自己才是《爱丽丝漫游奇境》影像作品版权的拥有者呢。
住在洛杉矶的时装设计师周二·巴森(Tuesday Bassen)靠出售她亲手制作的萌系小徽章、胸针和服装维生。2016年初,她接二连三地收到粉丝们的报告:时装连锁品牌Zara 用了你的设计!粉丝们很关心到底Zara有没有取得巴森的授权。
当然没有!一年内,巴森发现Zara盗用了她多款设计,直到她亲眼看见自己的一款胸针设计原封不动地出现在Zara商店里,巴森决定要采取行动。她找律师写了一封信给Zara, 希望它终止侵权行为。这封信花了她两千美元,这笔钱她得卖500个胸针才能挣回来。她的朋友兼设计合作伙伴亚当·库特兹的设计也被Zara盗用过,但是他选择了听之任之,因为觉得打官司也不会有结果。果然,对于如此显著的相似,Zara 给巴森的律师回了一封这样的信:“由于你客户的设计缺乏独特性,很难说全世界人口里的大部分人都会把这些标志和周二·巴森联系在一起。我们对此坚信不疑。同时我们也了解了你们所出示的第三方意见,但是那充其量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个投诉。考虑到每月我们网站的流量以百万计,这几个投诉和这个基数相比显然不成比例。”
Zara的律师为何这么牛气?因为在美国,时装类设计并不自动受知识产权法保护。40年前,美国制定版权法时还把美国时装业视为制造业,而不是创意产业,这也导致时装、时尚设计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要想保护一款设计,需单独申请“外观保护”, 昂贵又耗时,也只有大公司的经典产品有这个待遇,比如“爱马仕”给它的“铂金包”就申请了外观保护。这样,独立小设计师们就沦为大公司和大品牌们的免费创意库,随取随用。快销时装品牌比如Old Navy、Forever 21、Zara, 为了飞速把一拨拨的新品推向市场,在设计里“借鉴”的规模也很惊人,而这些都完全合法。
到了这一步,巴森虽然出不起两千美元再写一封律师信,但是她在社交媒体Instagram的账号有15.6万粉丝呢。巴森把证据以及Zara的回信贴到了Instagram 上,很快就被点赞38000次,Vogue、Buzzfeed 、英国卫报等媒体都开始关注此事。Zara 的母公司Inditex迅速反应,前倨后恭地联系巴森,说会联系她的律师,立即展开调查,把有疑问的产品都下架。
随着事态的扩大,湾区的其他独立设计师也纷纷站出来,亮出曾经被Zara 及其姐妹品牌盗用的作品,最后竟有20位设计师的作品被Inditex旗下的品牌盗用。这件事被媒体称为大卫和巨人歌利亚之战。不过,付不起昂贵律师费的设计师有了社交媒体上百万人的道义支持,全球最大的快销时装巨头也就不再是歌利亚了。
欧洲版权机构为艺术家追索原创收益
艺术家的群众基础没有时尚达人们那么强,不过艺术家们有他们自己的维权机构。希尔万第一次向给叶永青办展览的画廊投诉并没有亲自上阵,而是通过比利时作家、作曲家和出版社协会(SABAM),第二次是通过法国作家、作曲家及音乐编辑协会(SACEM)去交涉,这些都是著作权协会类型的组织,就像中国的文著协、音著协一样。SABAM成立于1922年,之前主要是为了保护音乐人的版权收益,现在则为所有类型的原创作品服务,在比利时有四万多名会员,包括作曲家、剧作家、翻译家、小说家、画家、雕塑家、摄影师、设计师等。2016年,SABAM为作者们追讨回了1.55亿欧元的版权收益。
SACEM的历史更久远一些,它也是作曲家们为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创立,业务逐渐延伸到其他创作领域。它成立于1851年,但是其雏形——为保护戏剧作品权益而成立的剧作家和作曲家协会(SACD)早在1777年就已经成立了。
欧洲各国都有这样的协会,挪威的叫Kopinor (挪威复制和影像复制协会), 成立于1980年,我的朋友赫尔格·荣宁教授在1998-2010年之间任Kopinor的主席。他说,著作权协会是文化良性循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有作者们获得了应得的作品收益,才能创造出新的艺术。Kopinor 无需得到艺术家的授权就可以代其去收集在挪威以及国外的版权收益,并将其返还给艺术家。Kopinor 还和大中小学、图书馆、各级政府部门和教会签订复印、数码复制授权协议,相关收益也会回到艺术家的手中。2017年,Kopinor的收入为3.5亿挪威克朗,支付给机构的著作权收益达 2.69 亿克朗,支付给个人的著作权收益达2900万克朗。
挪威的视觉艺术家们还另有一个组织帮他们维护著作权,这就是Bono (挪威视觉艺术家著作权协会), 他们不但代理2000名挪威视觉艺术家的知识产权事宜,还代理15万国际艺术家在挪威的版权收益。
视觉艺术的种类很广,目前有绘画、平面设计、工艺美术、雕塑、插画、纺织图案以及其他。版权保护的范围也很广泛:凡是以任何方式向公众传播、展示、介绍、散布艺术作品的物理复制版本或数字版本,比如说在书里使用这些图像或者用该作品来制作任何其他产品,或在社交媒体或网页上发布这些图像,都必须得到艺术家的许可,否则就属于侵权行为。版权意味着艺术家必须同意对作品的复制和传播,使用者要遵守艺术家提出的复制和传播的条件,比如说支付相应的版权费用。通过Bono获得的版权收益,65%支付给艺术家,35%则作为Bono的营运成本和发展基金。
我有个华裔挪威版画家朋友应国内某顶级美术出版社之约写了一本版画技术的书,出版社希望多使用最新的挪威版画作品,但是又没有支付版权费用的预算。我这朋友当然不能知法犯法,况且他也收过Bono代索回的版权费呢。这事最后也就黄了。
如果挪威视觉艺术家的作品被“借用”了,Bono 管不管呢?
Bono 是这样回答的:“版权所有人对于其作品具体的造型以及其个人创造活动的结果拥有权益。概念和点子不受版权保护。除非得到原作者的同意,对作品进行很少的改动或不作改动地再现,就算使用了其他的技法或移植在其他艺术造型门类上,都属于侵权。但是,就目前的法律来说,如果别人用已发布的作品来创造新的、独立的作品,原作的著作权拥有人无权提出指控。什么算‘新的、独立的作品’呢? 这就需要进行审美的全面考量和评估。在这个评估过程里,‘借’者有没有通过其个人的创造精神活动带来任何新的价值,以及这‘新的创造’是否压过了‘被借来’的部分,就是最重要的评估标准。”
此剽窃非彼“挪用”也
在“叶永青是否剽窃了希尔万作品”还在讨论中的时候,台湾策展人陆蓉之说过这是“挪用”,“挪用”是不需要和原作者打招呼的。其实呢,这话说得透着没学问。
挪用(appropriation )这个词源出文化研究领域。美国哲学家詹姆斯·杨对“文化挪用”研究最深入,他用这个词来形容文化被外人借用的情形,比如美国人借用土著印第安人的装饰和文化元素,这可能对文化的所有者形成冒犯,但是未必造成损害。
在流行文化研究领域也常用到“挪用”这个词,亨利·詹金斯用这个概念来形容流行文化的粉丝“盗用”大众媒体上的文本来创造他们的亚文化文本:同人杂志、同人故事、同人视频等等。这里的“挪用”是一种没有商业属性的社群行为,大众媒体和粉丝群体又是互生的关系,衍生产品那是多多益善啊,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在艺术领域,“挪用”的行为早就出现,梵高用油画复刻了许多日本浮世绘,中国画家从明清开始以临摹为学习甚至创作的手段。有意识地去“挪用”的第一人要算马赛·杜尚,他盗用《蒙娜丽莎》再加两撇小胡子。不过,就算拿现在的标准来衡量,杜尚的“挪用”让作品产生了新的意义和精神指向:反艺术,反审美,这个新作品仍是能够成立的。
20世纪70年代,一些美国艺术家正式把“挪用”发展成了一个观念艺术的门类——“挪用”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他们的作品。1981年,雪莉·乐文翻拍了摄影大师沃克·伊文思的著名作品《阿拉巴马佃农之妻》,作品名字就叫《仿沃克·伊文思》。雪莉·乐文复制的是伊文思照片的印刷品:一本伊文思摄影作品的目录。看着雪莉·乐文的《仿沃克·伊文思》,观众们不可避免地会想到一个问题:摄影这玩意儿到底是记录还是艺术作品呢?而这个疑问,就是雪莉·乐文“挪用”所创造出来的新意思和新价值。
由此可见,所有的“挪用”,不管是文化的,流行媒体和艺术的,或纯艺术的,是要观众意识到“借用”和“挪用”这个行为,知道它来自何处,来自何人,才成其为一种自觉的文化行为。先有哄骗受众的心,用别人的作品来充自己的灵感,就像用别人的房子充自己的财产,像黄眉老怪变出截流唐僧师徒的西天小雷音寺,这是哪门子的挪用呢?
还有些人表示,抄袭是最真诚的恭维。不过,被剽窃的艺术家千万别把这话当真。美国人约纳森·贝利本来是个诗人和媒体人,自从他发现自己写了六年的诗歌在网上被大量盗用后,愤而抄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误打误撞地成为了版权取证专家。他指出:“抄袭者们选择你的作品不过是因为他们正好能找到,而且正好能用上。抄袭者们之所以抄袭,并不是因为他们勤勤恳垦地找遍所有资源后,认为你的作品最好最值得拥有。他们要的只是一条走得通的捷径。就算那是一种恭维,难道你需要一个抄袭者的恭维吗?他们不管怎么说都是骗子,他们的恭维和奉承从本质上来说毫无意义。”
声明:网上天津登载此文出于传送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网友参考,如有侵权,请与本站客服联系。信息纠错: QQ:9528213;1482795735 E-MAIL:148279573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