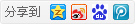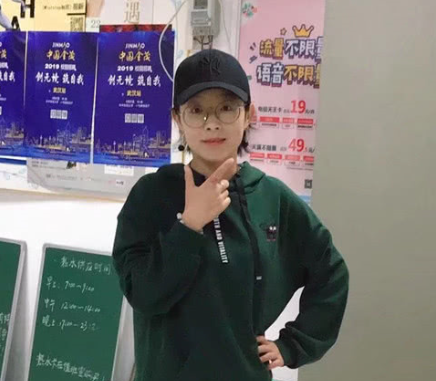叙事医学的治愈力:平凡的病人变成了有故事的人
时间:2019-04-01 09:03:48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导读]叙事医学讲故事的治愈力《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李明子本文首发于总第893期《中国新闻周刊》住院部16楼的患者刘军半夜突然醒来,跑出病房,咆哮着质问,“为什么不给我输血?”“这个为什么不能报销?”面对病人突然爆发的情绪,护士和家属都有点蒙。冷静之后,这名59岁的晚期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开始哭诉,“我睡不着,我能怎么办,我害怕啊!
住院部16楼的患者刘军半夜突然醒来,跑出病房,咆哮着质问,“为什么不给我输血?”“这个为什么不能报销?”面对病人突然爆发的情绪,护士和家属都有点蒙。冷静之后,这名59岁的晚期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开始哭诉,“我睡不着,我能怎么办,我害怕啊!”此前半个月内,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里与刘军同住的3位病友先后突发脑溢血离开人世,这加剧了他对死亡的恐惧。
“其实我不怕死,我是怕去不了女儿的婚礼。”这句心里话,刘军都没告诉家人,而是在16层东侧尽头一间小办公室里,向血液肿瘤科医生林晓骥哭着说的。如果等不到合适的骨髓进行移植,留给他的也只有半年时间。
刘军再次走进这间办公室,是在女儿婚礼后。几次访谈下来,他完成了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多次的诉说释放了内心的恐惧,此时已经明确知道等不到骨髓移植的刘军反而很平静。刘军不止一次提到当兵的经历,他希望自己能“光荣地来光荣地去”。因为患者提过要捐献器官,林晓骥开始联系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帮他完成了角膜捐赠的手续。病房里,刘军把红色封皮的证书端在胸前,和医护人员合了张影,一周后平静地走了。
“口述史让这些平凡的病人变成了有故事的人。”林晓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2017年到现在,他已经完成了36位临终患者的口述史记录,在诉说过程中,病人释放情绪、表达遗憾,甚至完成了对生死的思考,这些灵性的瞬间被林晓骥捕捉到,变成“关怀”的具体行动。
“医学是一种回应他人痛苦的能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教授、叙事医学创始人丽塔·卡伦在《叙事医学》中文版前言开宗明义,她主张医生要认识并尊重患者的悲痛。
在同名中文杂志《叙事医学》的创刊号中,中科院院士韩启德表示,“疾病最严重的结局是死亡,但如果患者看透了死亡,就不觉痛苦;疾病带来的痛苦主要是疼痛和悲情,是心理上的主观感觉,可能有的病人看好了病,心理上仍然感觉痛苦;但有的病虽然看不好,慢慢解除了病人的恐惧、恐慌,反倒不那么痛苦了。所以叙事医学是与医学人文紧紧连在一起的。”
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郭莉萍看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需求层次的提高,在老龄化与慢性病时代到来之际,叙事医学,或者说医学人文必然会成为一种趋势。
被忽视的“人文”
郭莉萍将“叙事医学”引入国内,实属无心插柳。2008年,她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医学分部访学,第一次接触到“文学与医学”课程,并在导师的建议下拜访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内科医生的丽塔·卡伦。
英国物理学家兼小说家斯诺早在1959年就警告说,科学和人文已经断裂为两种不同的文化,且愈行愈远,人为地割裂情感和身体的联系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病人在黑人平权运动、女权运动等民权运动的政治气候下,也开始要求人权受到尊重、平等拥有医疗资源等权力。在此之前,病人经历了近乎“非人”的待遇。当时,美国的医学院致力于把学生培养成极度推崇技术与工具的“科学医生”,医学生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病人就是具有异常的身体、放射学和实验室检验指标的客体。
卡伦对此感到,“只靠科学性医学是无法帮助患者与失去健康作斗争并找到疾病和死亡的意义的。”而患者讲述、医生倾听等叙事技巧可以拉近两者的心理距离,只有医生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患者的经历,医疗照护才能在谦卑、信任和尊重中进行。卡伦用“叙事医学”一词来表示一种具有叙事能力的医学实践,将其定义为“能够吸收、解释并被疾病的故事所感动的能力”。
“我是医生,我知道医生要什么。学者一直在提倡医学人文概念,医生则一直在质疑,都明白应人道地对待病人,但具体怎么做呢,谁也不知道,叙事医学就是医生们做的事。”卡伦在接受郭莉萍访谈时举例说,比如教医学生细读文学文本,培养学生关注细节、理解不同叙事视角等能力,并在医疗过程中将这种“叙事能力”迁移到“倾听能力”上,理解病人患病经历,也就是“共情”,从而尊重、关怀患者。
卡伦的话深深触动了郭莉萍。中国推行医学人文教育可追溯到1980年代。“当时以批判为主,学者们提出医学不该只关注医疗技术、忽视患者作为人的感受。”郭莉萍介绍说,但这样的声音并未得到医护人员的普遍重视。1990年代,医学人文教师到医院给医学生讲伦理课时,临床导师甚至公开和学生说“那些课不重要”。
2012年,记者出身的凌志军在《重生笔记》一书中记录了自己抗癌求医的感受。当时凌志军花了300元挂上专家号,耐心等待3小时,终于在下班前几分钟见到了“专家”。凌志军强打精神试图叙述病症,但专家并不感兴趣,而是拿着核磁共振胶片对着年轻医生讲课般滔滔不绝,凌志军形容“这情景就如同你花了一大笔钱之后来到期待已久的埃及金字塔,经验丰富的导游把钱揣进口袋却视你如无物,扭过脸去教导他自己的儿子如何谋生”。
2011年11月4日,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在韩启德的召集下举办了首届叙事医学座谈会,郭莉萍第一次在国内公开介绍了“叙事医学”。叙事能力和人文素养不仅是对医生素质的要求,更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据原扬州市卫生局局长王方松撰文,80%的医疗纠纷直接系因医患交流沟通不良所致,其余20%与医疗技术有关的医疗纠纷,也都与医患沟通不到位密切相关。《暴力伤医事件大数据研究》显示,中国暴力伤医事件数在2013年达到顶点。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全国医闹事件共发生17243起,比五年前多了近7000起。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正式施行,医闹入刑,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对外呼吁医闹入刑,从宏观上来保护医生,但关起门来,要严格要求医生,重视人文教育。”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医学人文的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郭莉萍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说,现代医学让医生对疾病的认知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因此更需要医生与患者沟通,弥合信息不对称,并尊重患者的感受,仍要回归到100多年前美国医生特鲁多提出的“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别忘了,医疗的服务对象是人。”郭莉萍说。
2015年,郭莉萍将卡伦的著作《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同名杂志《叙事医学》于2018年7月创刊。让郭莉萍备感欣慰的是,许多医疗单位和医生个人在知道叙事医学的概念之前,已经在身体力行了。
人文关怀实践
林晓骥以前给肿瘤患者开止痛药,家属不安地问“为什么病人还是觉得疼”,他就会很冷静地从医学角度解释,“2小时候后起效,正常,熬熬就过去了”。但7年前陪伴癌症晚期的父亲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经历,令他真切体会到了患者的无奈与痛苦。回到工作岗位后,再次面对病房里这些癌症晚期患者,林晓骥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恰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准备引入志愿者服务,经过医院团委同意,他组建了温州市第一支致力于临终关怀的志愿者团队,以医学生与医护人员为主,累计服务了300余位临终患者。
在志愿服务记录本中,林晓骥发现患者总是喜欢聊自己的过往,“人生回顾,这不就是口述史嘛。”随后,他查到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护理和助产学院教师米歇尔·温斯洛从2007年起一直在为临终患者做口述史,内容录音并刻成光盘送给家属做纪念。
“患者可以从中提高自尊、获得价值感、赋予生活意义,临床实践和健康研究可以从叙事总结中进步,工作人员更充分地理解了疾病对患者身份和生活的影响,志愿者也可以在活动中获得交流、记录等技能。”米歇尔·温斯洛在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的邮件中介绍道,12年中她的志愿团队完成了400多个访谈,这种被称为“谢菲尔德模式”的口述史项目已经被英格兰与北爱尔兰等多个地区所采用。
林晓骥也看到了口述史对患者、医护人员和研究的三重意义,于2017年正式在血液肿瘤科做临终患者的口述史。访谈分为三部分,从患者的人生回顾开始,挖掘他们人生中的高光时刻;第二部分是林晓骥最为重视的,探讨生病对患者身体、心理、社交和家庭关系的影响,信仰是否改变,以及对死亡的看法;最后一部分,请患者评价医疗工作。
在2018年底接触到“叙事医学”后,林晓骥开始寻找这个理念与自己实践的结合点。在他看来,从医生的角度通过“叙事医学”培养人文素养,与直接服务患者的关怀行动,是殊途同归的,最终的受益者都是患者。
作为医疗界公众人物,凌锋一直提倡要培养医生的人文精神。她为此提出了“生活查房”,鼓励医生们每天循例查房之后再到病房溜达溜达,平时没有时间解释的医疗问题可以在这时和患者详细聊聊,或者单纯和病人唠两句家常,让患者感受到医生的关怀,而不是一直高高在上。
在2011年的首届叙事医学座谈会上,作为嘉宾出席的凌锋第一次听到“叙事医学”的概念,通过写叙事病例(也叫平行病历)、细读文学作品等方式,培养医生叙事能力,从而见证、关切患者的苦难。这给她正推行的人文教育提供了新的抓手。
从2012年起,凌锋要求神经外科所有年轻医生每人每月写一篇叙事病例,包括住院医生、进修医生和研究生。起初,很多年轻医生是被逼着写,慢慢地,写作成为习惯。与患者交流的细节成为对照自己行为的反思,“人文”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种子就在医生心里生根发芽了。
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兼缺血性脑血管病区主任焦力群曾把自己的经历写在了年鉴上。2001年,焦力群从山东某医院考到北京,成为凌锋的博士研究生。刚到宣武医院时,焦力群跟病人谈话时总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翘着二郎腿,不止一次地在办公室边抽烟边跟病人说话,“随意的语调,傲慢的态度,冷漠的眼神,恐怕是当时很多医生的共同点”。焦力群写道,十年后,每周三上午的门诊,他都会看到下午1点多,病人不见得是最多的,但每位病人的疑惑他都会心平气和地解答。
焦力群自己也说不清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十年前,他看到医生推着病人做检查时会倍感惊讶,心想“这是医生该做的吗?”十年之后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如果一个医生没有推重病人做检查的经历,他一定不是临床医生,或者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医生。”焦力群在年鉴中写道。
写作对于医生来说也具有一定的治愈力。《美国医学会杂志》2015年12月8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披露,对包括17000多名正在培训中的医生所做的分析发现,在担任住院医生期间,有近三分之一的人筛检呈抑郁症或抑郁症状阳性。“医生是抑郁率很高的职业,他们要承受非常人的精神压力。”郭莉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面对日常生活里的不公或挫折,他们需要回答自己,要成为一名怎样的医生,如何坚持自己的职业操守,这些都是医学中人文的东西,把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念头写下来,其实也是被迫深入思考并自恰的过程。
也有人质疑,这样做真的能改善医患沟通吗?
“中国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系统的研究,但过往研究显示,确实可以帮助改善医患关系。”郭莉萍调出一组数据:美国缅因州人文理事会的“文学与医学”项目,每月组织一次读书会,邀请文学学者带领组员讨论,并邀请第三方机构对项目效果做研究。2008年11月,南缅因州大学埃德蒙·马斯基公共服务学院博士布鲁斯·克拉里的研究结果显示,通过文学学习,成员对病人的同理心提高了79%,沟通技巧提高了58%。
如何落地
“这难道不是不务正业吗?”“这有什么意义?”多年来,对叙事医学的质疑声从未停过,在郭莉萍看来,最大困难还是如何让医生理解叙事医学。
平行病例是培养医生叙事技巧的手段,并不等于叙事医学本身,而“叙事”也不等于让患者滔滔不绝地倾诉,目的是让医生观察、体会到患者的病痛,从而更人性地医疗。说白了,叙事医学是实现医学人文的一个工具,弥合先进医疗技术和患者的最后一公里。
门诊医生都有被同一个问题问无数遍的经历。一上午接待几十位患者,高强度的工作会把人的善意磨平,暴露出最理性、冷酷的一面。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住院医生陆夏也有类似感受,绝大多数情况下,病人问到一半他就已经想好了答案,但他会等病人问完,然后礼貌性地等待两三秒,再回答。如果遇到说话刹不住车的患者,陆夏会在心里默默计时,如果说了3分钟还没有切入正题,他会礼貌打断,“我先解释一下你刚刚说的问题”。
“如果没有医学人文的训练,我可能会直接打断病人的提问给出一个答案,10秒就能搞定。”陆夏说。1984年《内科学年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显示,医生平均在患者开始说话18秒之后就开始打断他们,觉得他们说的没用了。但如果让患者把自己认为应该让医生知道的信息都说完,平均只需要60秒。从18秒到60秒,医生只节省了42秒,但是患者的感觉却从满意变为不满意。
“患者心中的理想医生总是有很多明确的标签,医术高超、关心病人,说话得体,最好还能有点幽默感,如果长得好看就更加分。”陆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医生心中的“理想医生”却没有统一标准,陆夏理想中的医生应该是在手术台上极为冷静、在与患者沟通时极为感性的存在,但科学和人文本来就是矛盾的,如何取舍实则是个人的理解与选择。
“中国医生群体同质性低,也是对叙事医学理解差异过大的原因。”郭莉萍说。她曾到一所医科大学讲课,校长自豪地对她说学校每年招收3000多名临床医学生,这使她感到十分惊讶,北大医学部扩招后的人数也不过300多人,全台湾每年培养的医学系毕业生才1300人左右,大陆高校大规模招收医学生的现象绝非个案,很多医学院的教育质量值得怀疑。
另一方面,也不是医院所有科室对“叙事医学”的需求都一样。老年科、肿瘤科、疼痛科、精神科等科室,患者对人文关怀的需求更高,因此医生对“叙事医学”需求也更高。大多数外科对“叙事医学”的需求则集中“解释说明”的功能上,例如通解释治疗方案,如何告知病人知情同意书等等,这需要对症下药。
《健康管理蓝皮书:中国健康管理与健康产业发展报告(2018)》指出,中国慢性病发病人数在3亿左右,其中65岁以上人群慢性病负担占50%。2018年3月31日,第二次叙事医学座谈会上,许多慢性病的医生都表示需要更多的时间与病人交流,他们也是最为重视病人叙事的群体之一。因为在医院里跟病人交流的时间有限,一些慢性病医生就建立了病人的微信群,病人在群里讨论各种问题,医生回复,在门诊以外的时间帮助病人管理疾病。
“人得病之后,尤其是慢性病,比如癌症,对患者来说,疾病本身不那么可怕了,可怕的是不知道该不该活着,或者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但如果真正理解了,即使带病生存,也可以用一种敞亮的心态去生活,这些需要和有专业知识的人交流,医生和病人交谈,对病人的意义非常大。”郭莉萍说。
“我们国家开展叙事医学也有不利的地方。”韩启德接受《叙事医学》专访时曾分析,中国的优质医疗资源过分集中在城市大医院,病人都赶到大医院看病,医生没有时间精力与病人沟通,而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与签约家庭医生本来更有条件开展叙事医学,但却缺乏激励机制与病人的信任,其人员素质也参差不齐。
韩启德认为,关键是要深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力量,实现基层全科医生和签约医生首诊制。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为叙事医学的全面开展奠定合适的制度基础。但是,他同样指出,并不能等待到那时才着手开展叙事医学,在现有条件下就应大力提倡。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11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声明:网上天津登载此文出于传送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网友参考,如有侵权,请与本站客服联系。信息纠错: QQ:9528213;1482795735 E-MAIL:1482795735@qq.com